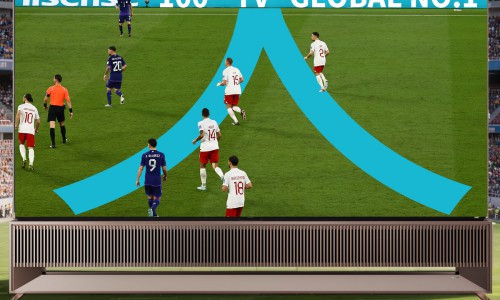浙派绘画
[内容摘要]历史上的浙派绘画,是从一个区域开始发展并迅速成为一个风格鲜明的艺术流派。当时还有另一些不同的绘画流派存在,也有着颇为类似的情形,如吴门画派。但吴门画派又与浙派有所不同,比如很多画家艺术活动时间较为接近,可以共同研究画理画法,这对于推动自身画派形成极为有利。而浙派有代表性画家,其活动年代相隔久远,客观上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势必造成浙派绘画理论体系的某种欠缺,由此出现的问题是,一旦受到不同门户攻击时,便无招架或反击之力,特别是对推到与文人画对立的书画市场中面对各种利益,极易陷入尴尬境地。这无疑制约了浙派艺术的后期发展。
[关键词]浙派绘画 南北宗论 文人画
作为明代画坛上的一支劲旅-浙派绘画,由于其自身艺术语言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在当时堪称一枝独秀的表现流派,一时间,在画坛上占尽风光。无疑,浙派在传统绘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遗憾的是到明末清初,画派之间的争斗日趋激烈,使得浙派绘画被推向与文人画的对立面而跌入低谷。相关的史论研究多以吴门画派艺术成就来代表明代绘画,此外还包括提出“南北宗”论的董其昌和松江派等。这种一味抹杀浙派绘画的艺术成就以及对于该画派在中国绘画史的独特贡献的漠视态度,是让人觉得不尽客观的。这也反映出明代画坛的门派之争较唐宋元时代更加激烈、复杂。
浙派由鼎盛到走入低谷的这段时期,吸引了许多美术史论家关注的目光。《中国绘画史》的作者俞建华先生对此发表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士气日少,作家气愈多,寝假而为霸悍之态,加以浙派作家,虽曾盛极一时,虽多非文学之士,故不能著书立说,阐明画法上之优点,及受异派之攻击,亦不能反唇相讥,攻异派之弱点,因之异派之讥评逢起,而浙派自身亦渐以不振矣。”
文中列表是浙派、吴门派与松江派几位代表人物生卒年考,从中可看出每个画派自身的结构关系。
从表格所排出的三个不同画派以及画家创作活动时间顺序上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吴门画派几位创始人最有可能在一起切磋画艺,讨论画事,特别是沈周与文徵明这对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他们通过参加各种书画雅集活动,在一起交流画理画法,才使得各种不同艺术观点逐渐趋向一致。这些便利条件足已让吴门画派发展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另外像松江派的董其昌、陈继儒,他们的出生与死亡时间更为接近。在推行南北宗论包括贬低浙派绘画的措词上,二人的态度更是一致。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浙派最具代表性的画家,都不在同一个时段内从事艺术创作活动。因为他们中的每两个人的出生年代都相隔得很远,不可能在一起交流绘画创作。这一状况势必对浙派绘画日后的发展有诸多不利。画家戴进辞世时,吴伟才3岁;而浙派殿军人物蓝瑛,其艺术创作活跃期已接近明代晚期。这就是说,浙派绘画从开始到成熟之间,其中成员活动松散,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基本是后人对前人绘画风格的简单的摹仿而已。而这一切又势必影响到画派自身艺术深度的探索,难以“做强做大”。那么,在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这些画家其自身弱点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下,极易受到来自外部不同门户的攻击。加之多数浙派画家理论研究上的不足,浙派的发展自然是更加艰难。正如俞建华先生所言的那样,像锻工出身的戴进,至多能写点诗。吴伟这方面就更欠缺了,他的大多数画作只题“小仙”二字,或也有旁人落的款,如《歌舞图》等。自小被别人收养的他,虽凭借个人天资和努力一步步走向成功,直至名声大振,但因社交活动频繁,又难免占据他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据记载,吴伟不是作为官府豪门的座上宾成天应酬作画,就是作为声色场所的寻常客狎妓寻欢,生活与品行如此狂放不羁,还有何闲暇兴致静下心来作画理研究及诗词写作,充实绘画内涵和文学修养?而另一位活跃在明代后期的蓝瑛,因其“出身寒微,从小就放弃了学业”。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句看似“豪言壮语”的“古人未有书,先有图,图何必不名家”,竟出自于当时已名声大噪的画家蓝瑛之口。此语有惟技能、轻文化之意。如此狭隘之见,一旦授人以柄,便会招来各种人身攻击,如“浙派属于没有文人笔墨的行家画,其蒙养低下不足以论艺”等等。特别是当出现各种围绕“南北宗”论不同层面的攻击时,多数浙派后继者都无力反击。本来绘画这一领域极易出现门户之见,各种谩骂、攻讦之端,多是某个画派为求得自己是当下画坛一杆旗帜而百般挑剔其他画派,大造贬低之事;以为这样就能使别的门派在画坛难以立足生存,而自家就能成为当朝画界之楷模傲视天下了。
相比于同一个时期其他画派普遍重视理论研究,浙派画家却疏于画理。故一旦受到不同门户攻击,总是无力应对。在维护本画派的社会地位及其声誉方面,由于缺之有力的理论武器反击对方,浙派画家们总是处于不利的位置。
从大量记载中国画理的书籍中,很难找出与戴进、吴伟相关的或他们的追随者对绘画见解的只言片语,更不用说长篇大论的理论纲领了。是编书者疏忽,还是另有其因?这就得从相关的画史文献入手,才能有所了解。
我们知道,起于明代前期至中期近200年历史的浙派绘画,曾有几位画师被授予锦衣卫,包括画状元吴伟。作为朝廷鹰犬专政机构的锦衣卫,少不了去做一些祸害在野文人的坏事。就这点,足已让他们为青史所不容,以招至天下人的怨恨。那么其一,关于浙派的画论要在画界或同行间传播开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其二,洪武至崇桢270年问有记录在册的画院画师共70余位,但几乎没有相关的理论记录。和他们相比,在野的明四家或松江派的董其昌、陈继儒却能立论史。难道朝廷规定了只要戴进、吴伟和蓝瑛这些画师成天埋头作画,不作学术研究吗?
唯一的解释是,朝廷不允许这些画师们在由他们钦定的绘画风格这一问题上对南宋一类挺拔的画风、画法随意地改变。如果这一推论能成立的话,就不难理解明代确立的宫廷绘画标准,是以南宋院体画法作为当朝艺术的唯一准绳,舍此之外的各种绘画风格都难以立足南宋画界。故一花独放的现实就是继承南宋画法的结果。于是,凡人物、山水、花鸟画,皆宗法马远、夏圭的审美趣昧发展。
由此看出,明代宫廷画师,在艺术品制作上很难有创新的自由,这也包括理论的创新。相反,一些难已被宫廷画院录用的在野画家,尤其明代中晚期出现的不少在画史上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师,除了拥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外,在画理方面也有所建树。
浙派绘画不乏精湛的技艺,独缺少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以戴进、吴伟和蓝瑛为代表的浙派绘画,由于其出生年代等客观事实决定了他们在形成这一艺术体系时,不可能像吴门画派的沈周与文徵明那样拥有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的关系,也不可能像唐寅和仇英那样有同乡的情谊。另外,像晚明的董其昌、陈继儒等把持松江画派的“画中九友”,其艺术趋向更是一致。相比而言,后起的这两个画派,其画家之间直接对话和相互沟通作画、共同的活动机会更多。因此,他们的一些理论见解和学术主张都完整地保存在各自的文集里,如沈周的《沈石田集》,文徵明的《文徵明集》,以及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寓意录》,陈继儒的《偃曝余谈》等等。
显然,明代后期是文人画理论得以迅速传播的时期,对清代绘画的形成也有直接的影响。再者,被明代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宋代水墨技法,以及包括像郭河阳的《林泉高致》等一些对后世绘画影响深刻的理论,都是基于画家创作实践的艺术感悟,言之有物,有些还针砭时弊。而浙派绘画体系呈现给世人面前的,只有那一幅幅似烟云密布的水墨画作,理论上却几近空白。后来者也不能很好地从师学体系那里发掘总结。不过,这不足为奇:一是浙派绘画这一叫法是由后明董其昌等人提出的。如果是根据画派问的各种利害关系来决定今天评价其好或明天评价其坏,那么有关浙派的是是非非就全操纵在这些文人的言谈中了。又因属不同流派背景下,各种门户之见始终难以回避。这就很容易理解后来出现的一片对浙派绘画的各种指责。二是这个在明代前期和中期有巨大艺术影响力的画派,最后竟一蹶不振。这并不是他们的画法带有什么政治问题而受朝廷或社会的排斥。相反,戴进与吴伟二人先后作为宫廷画师为朝廷效力,自然不会受到排斥。即使戴进一度离开画院回到故里杭州城,过着边卖画边授艺的日子,依然没有背离北派画法,挥笔运墨上还是取劲利的斧劈皴法表现。
如《春山积翠》一画,不仅墨色酣畅,水气充盈,节奏明快,而且与别的浙派绘画一样,作品展现的是一种世俗亲和的气氛。这一点正是打下大明江山的朱元璋及其皇子皇孙们所欣赏的,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的情景图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派绘画就是明代宫廷绘画艺术的另一种体现,既有继承传统又有发展当朝艺术的地方,但又不完全属于宫廷绘画模式,有相对自由的表现空间和自己的语言风格,应当算是当时最为上乘的绘画样式。另外,明太祖是一个从草根阶层奋斗到统治者地位的君主,他对绘画艺术既不在行,也不想去了解高深的文人画理念;只要有精神向上的视觉效果,并且能为天朝政治服务的绘画风格,就是他所看中的,就是一个字“好”。故元代那种虚静内参的画面一概不被他看好。于是,从前明乃至中明这段时期,元四家的绘画技法几乎难成一家之法,更不可能进入宫廷画院,至多只能在民间被少数人推崇一下。
戴进偶尔仿了一点元季画法,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长松五鹿图》,也是在一度离开京城和画院关系不大的情况下学了几笔的,但最终还是不能替代为其一生朝夕揣摩的南宋那种水墨苍劲的马、夏技法。虽然,画面不少技法有得黄公望、王蒙诸家笔意墨法之迹,却反而不及他所仿郭河阳在山水画里追求的“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的那种艺术境界的另一张画作《踏雪寻梅图》的艺术水准了。于是,他很快就放弃了元季画法。
至于吴伟,就更不去接触和学习元四家法了。吴伟比戴进更受宠幸,曾先后三次得皇上诏见入宫作画(但最后一次还未进宫就因醉酒猝死于路上)。因其画技享誉京城,为显贵作画机会就更多了。除少部分人物画,他的多数山水画作全然是马、夏画法为一体的程式表现,体现出阳刚雄健的水墨风格,无不超越于南宋诸家。在用笔节奏上,其画作充溢着一种风掣电闪的视觉感,画里画外透出一股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笔墨气势,如《灞桥风雪图》《渔乐图》以及人物画《东方朔偷桃图》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以马远、夏圭的山水技法,挥笔运墨中勾写衣纹线条,使人物写意法更为鲜明突出。
由此看出,与从不过问绘画艺术的元代统治者相比,明代所流行的绘画风格都是由朝廷钦定的一种画法,被画家竟相仿效。这是从政权统治需要的角度对艺术加以干预的具体表现。所以推出马、夏水墨画作为整个院体画法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当时画坛的“主旋律”。故戴进能够被晚明的董其昌推为“本朝画流第一人”,不完全是因其技法能被董其昌所推崇赏析,而是在当时为迎合朝廷政治需要所做的评价而已。戴进的影响范围之大,已越出江浙一带,包括吴门画坛领袖沈周也曾虚心学戴进画法,“尤其是他那粗笔山水,许多都有与戴进相通之处”。但董其昌、陈继儒这二位在艺术见解上相一致的松江派画家,却从未对浙派艺术风格作出客观深入和正确的评价。而就当时的松江画派,还不具备与满朝上下影响力相当的浙派以及已然立足画坛的吴门画派这二大画系相抗衡,故只有从理论上说三道四,发发牢骚。
不过吴门画派最终得以躲过一劫,原因是董、陈及沈颢若干人推崇的“南北宗论”,其理论核心与沈周、文徵明等一样也都是曾经效法元四家的,所师者皆同一出处。如果说他们之间艺术上有大的区别,是因为吴门画派通过学元代画法后,能融汇于外师造化之中。而当时浙派的祖师是李唐、郭熙、马远、夏圭,都是以斧劈皴入画的北派巨匠,与董其昌处处所推崇的南宗山水图式相去甚远。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董其昌欲借推行“南北宗”论,把自己立为画坛之霸主,使松江派不致于天天在影响力强大的浙派下过苦日子。因为从董为官一生来看,有巧取豪夺的一面,包括董家在松江是富甲一方的豪门,有良田万顷,势强力大,甚至发生过强抢民女一事,惹得当地百姓聚集起来烧毁其房宅。其人品不端和强权霸道的一面,也会展现在他的绘画创作中正如博宝鉴定专家单国强在《中国美术·明清至近代》一书中所指出的“后来他(指董其昌)越来越强烈地以画坛正统自居,直接与元赵孟頫、明文徵明相比,宣称“同能不如独胜”。“董其昌的自负性格和使命感,使他想超越吴门画家而与赵孟頫并驾齐驱。甚至力图超越赵孟頫,直追王维、董源。摒弃纤谨、粗犷、精工的画风,创造生秀淡雅的新格。”
虽然“南北宗”论强调了绘画创作中的文人画内涵,但人们也可以通过另一角度考察当时为什么能产生这一画论的历史背景及相关动机。正是受“南北宗”论影响,不少画家、画论者们纷纷把以戴进、吴伟为代表的浙派绘画与文人画完全对立起来,视为行家画,根本不能为当下画坛所仿效。今天看来,董氏这一套理论体系攻击性很强,有煽阴风点鬼火之力。不过以他当时松江派的气力,还不能彻底颠覆浙派绘画。但后来,借着康熙皇帝对董其昌书体大为赞赏并以文人画理论排斥以戴进、吴伟为代表的浙派绘画各种调子,一时间成为画坛主流,逐渐使后来学习浙派绘画的画家不能专心于其法,担心在画坛吃不开,没有市场,没有观众。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谈不上如何如何在师承戴进、吴伟绘画的基础上有所开拓了。最终导致浙派画法江河日下,甚至把吴伟原本粗放雄强的笔势,简单理解为粗率行笔,不究笔意法度。
其实,在吴伟一生的绘画创作中,一些描绘人物的小写意画如传世作品《铁笛图》及《歌舞图》,呈现构思巧妙、造型严谨、笔墨变化细致的艺术效果,尤其画中人物神情刻画细腻,这是明代人物画史上难得一见的力作,绝不是后期那些无端指责浙派绘画是粗俗板塞、毫无艺术美感的论调所能否定的了。总之,他们不是以客观公正的角度评价浙派绘画艺术,而是要将它置于一种气竭息衰的境地,再不值得大家那么推崇的画法了,最终让马、夏这一路北宗水墨语言风光不再,悄然无息,那么整个浙派画法就此无人问津。
说到这里,不禁让人对浙派绘画的命途扼腕叹息。试想,一个能够在中明时期于杭州至南京这一经济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域成为影响力极广的画派,却因为受到其他政治性手段的干预而衰落。而始作俑者董其昌却声隆天下。北宗画法被各种倡导文人画者有意贬低为无文人学识气息、无文化内涵蒙养,用心何其极?可见当时画坛的门户之争有多么激烈。使以斧劈皴法为主要表现语言的苍劲有力的水墨绘画风格一度在北宋、南宋这两个时期内发展得最好。李唐《万壑松风图》、马远《踏歌图》等这类手法写实的画面,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俗风情的内容。通过使用一种入世的细致描绘的手法,使其在当时社会各阶层中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戴进及当时一大批明代宫廷画师正是本着共同的艺术追求、共同的艺术兴趣,才能将北宋至南宋这段过渡期间所形成的这一艺术手法继承下来。比如与戴进一同成为宫廷画师的倪端,就是运用这一写实效果突出、画面再现力很强的斧劈皴画出了《聘庞图》。以工笔、写意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进行的艺术创作,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朝统治者对绘画的一贯方针,也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逐步繁荣稳定而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而且,戴进在基本坚持这一苍劲的水墨风格前提下,形成了与倪端不同的艺术构筑。譬如,他还画了《达摩至慧能六代祖师像》,其中所有勾斫、染墨、构图法则都与倪端《聘庞图》明显不同,其水墨效果及书写性表现都是《聘庞图》一画所不具有的:这些手法在他的《踏雪寻梅图》上体现得更为精熟老到。从画面上看,倪端还是完整地继承了刘松年画法——一种稳健和谐的绘画效果,更偏向塑造;而戴进却从马远、夏圭那里汲取了简洁、挺拔的风格语言,更趋向写意。
之后的吴伟也走了一条与戴进艺术取向基本相同的表现路子。可见,运用斧劈皴这一劲利有力或斜皴或横卧皴,展现了明代水墨山水绘画雄强开阔的艺术风貌,是当时整个山水画艺术表现的主体语言。其特有的艺术表现力独据画坛200多年,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古人所创造的各种山水画皴法,无论是在表现风格还是语言形式上,都在不断地丰富艺术的审美趣味。
董其昌“南北宗”论未出台之前,皴法是古人外师造化并通过写生观察最终形成的以描绘山川自然形态并融合了画家艺术禀性的表现技法,其趣味审美的多样化,无不生动具体地反映在整个山水画形成的漫长过程中。无论是南宗的还是北宗的不同皴法,这两种技法其问并无优劣、高低之分。但在董其昌名声地位提高后,相关“南北宗”这一论题所展开的各种对北宗也就是以斧劈皴为皴法之末流并且不能登文人画大雅之堂的讨伐,使那些被他们指定为南宗的披麻皴、解索皴成了日后山水画坛一技独秀的技法。同时,废斧劈皴且使其难在画坛上生存下去,这也使我们不难理解从明末到清初,为何处处宠罩在“家家一峰,人人大痴”的摹古风气中。
明代前、中两个时期还有一些师法自然的山水画创作:而后来备受“南北宗”论影响极深的“清四王”,干脆身体力行地推行以复古为能事,完全不提艺术贵在独创这一创作准则,只取古人粉本中所谓南宗画派的元四家技法为准绳:并且狭隘地把不同于此——由戴进继承李唐、马远、夏圭以斧劈皴表现特点所形成的浙派绘画,统统拒绝于画界之外。怪不得后人对明末清初因循守旧的山水画风厌恶之极,是不无道理的。
明代画派之争这一现象,远超于以往各个时期。于是出现了为达到推翻一个画派后树立自己体系而处心积虑制造各种借口或理由。“南北宗”论的出笼,其实就是明末画坛掀起的一场犹如政坛上的“文字狱”。在明代初期,朱元璋、朱棣就曾大肆制造“文字狱”,杀了不少文人墨客。而后随着明王朝政权逐步稳固,经济走向繁荣,统治者由最早动不动就取人性命的残酷血腥镇压,演变为另一种让社会各个层面为了各自所需的空间,而出现的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游戏,如东林党与宦官庵党之间的权利斗争,然后朝廷再加强左右分化以取得最大利益。于是,这种变幻无常的政治局面,也会对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产生不小的影响,如愈演愈热的文坛流派之争到画派间的门户之见;回顾唐、宋、元三个历史时期,此类现象较少。另外,随着江浙一带经济繁荣百姓生活水平逐步上升、民间对艺术品需求量的不断扩大等原因,其经济利益无时无刻不牵动文人墨客的商业神经,如与戴进好友的画竹高手夏昶,其墨竹在市场就销售得相当好,时有“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誉,足见整个明代社会绘画市场的活跃程度也是以往各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所以,画派问的门户之见,既有风格流派之争也有商业利益的权衡。假如“南宗画法”最终能取替“北宗画法”,顺利地成为社会主流画法,那就能轻而易举地完全占有市场,那么以“南宗法”入画的画家就能衣食无忧,日子好过了。所以“南北宗”论推出的背后,其实也有社会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这一点不同于元代的文人墨客。在元代,一是朝廷不养画师,二来在朝廷不关心艺术的情形之下,多人退隐山林、浪迹江湖,可以借题诗画发点小牢骚,如倪云林。但这种太放任自由的艺术性情,是无法被明初期统治者所容忍的,更不可能长期发展下去的。所以,成名于元代的王蒙和倪瓒,一旦遭遇明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就要倒大霉,这一情形无不让一大批朝廷画师内心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谁还敢在画面上随随便便写这题那?至多就以画家名号简单落款,生怕被朝廷豢养的一大批宦官太监从字里行间挑出是非,惹来杀身之祸。而元代画家包括明中后期在野画家,就能随意地在画上出现不同款识,可以是诗词也可以是论画或随笔的各种感慨。
到了明代后期,统治者以较柔和的手腕,让宦官把握朝政,文坛开始有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如明末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文小说,像冯梦龙的《拍案惊奇》和吴承恩的《西游记》等。显然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一种较为自由的表现手法,绘画艺术也基本是沿着这一形势发展的。在戴进、吴伟及其他吴门画家陆续告别人世后,另一些社会影响还相对较小的人物才由此走向历史舞台,如松江派的董其昌、陈继儒及武林画派的蓝瑛等。无论是文人画家还是职业画师,他们对长期由宫廷指定画法多少有些不满。所以当董其昌诸人及时地抛出“南北宗”论时,就让他们感到另一种绘画表现的相对自由。如最初还是以戴进、吴伟画法为宗的被称为浙派殿军的蓝瑛,后来也转向了学习元四家画法并加以创新。
蓝瑛受“南北宗”论影响较深。史载,他曾独自一人到松江拜见董其昌,并在晚年接受董的建议转向倪大痴、黄一峰、吴仲圭甚至上溯荆浩、关仝的所谓南宗画法,而较少仿效戴进、吴伟画法包括属于北宗法的其他宋代画家的技法风格。
当然,一个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大多是由他个人禀性及创作趣味取向所决定的。但理论上如“南北宗”论的出台,对画坛的冲击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因为它容易成为一种导向,使一个处于鼎盛期有200年历史的画法最终不能得以发扬光大一个画派或一种技法,要保持持续的艺术生命力,就不能单靠开创者的一生努力,还必须有一代又一代的后续者的完善发挥,使之尽善尽美。世事无不如此,绘事更当如此。
再看看以董其昌、陈继儒为代表的松江画派。无论是章法、风格或技法,实不足与浙派或吴门画派相媲美。特别是董其昌的某些青绿山水画,程式化不仅明显,创造性也不多,几乎都是摹元人画法,或简单地向装饰手法靠近而已。包括陈继儒的笔墨也很单一,毫无师造化的革新气象。他们二人对陈陈相因的清代画风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就凡出笔都要寻找其出处这一点,恰好为后来者如“清四王”所中意,最终只能使绘画陷于一味摹古走向僵化无聊的笔墨游戏中去。
中国哲学往往围绕“以柔克刚”去阐释宇宙世界的各种规律、现象。儒、道、释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核心思想,文人画正是这一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浙派取刚硬的北宗画法有所不同的是,南宗画法的语言风格相对柔和。若以华夏文化现象作进一步探析,“以柔化刚”的艺术趣味有更广泛的接受层面,犹如常人处事总是讲究以和为贵,不必处处较真。那么相对于一味刚硬彪悍的用笔风格,阴柔清秀的笔墨有时会拥有更多的欣赏者。应该说董其昌有过人之处,他就是抓住了传统哲学的基本核心,将“刚”与“柔”这一自然界现象引入绘画中,并与山水画“南北宗”理论联成一体。借南宗的较为柔和的皴法使笔墨表现力更胜一筹,就能直接把北宗的那种相对刚直的笔墨语言贬为绘画之未流,一扫而尽,使之无画坛立足之地。如《艺苑厄言》曰“传伟法者,平山张路最知名,然不得其秀逸处,仅有道劲耳”。更有《绘事微言》直说浙派后期几位画家“皆画中邪学,尤非所当”,更有“此等虽用以揩抹,犹惧辱吾之几榻也”。语锋之激烈,无一不是把浙派绘画从开山鼻祖到后学者说得一无是处,这还有发展的必要吗?最终使浙派在一片讨伐声中,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何良浚此话还只是低层面的,如同两个人的一般争吵,还不可能完全置浙派绘画于死地,即便他已是明代中期著名的画学批评家。但董其昌“南北宗”论则更具煽动性。一是,浙、吴两大画派重要人物都已不在人世,特别是戴进与吴伟;其时画坛朝野正无领袖。而董其昌曾官至左侍郎,掌国事监司业,财大业大的他,对文人画的一切言谈具有不同于他人的影响力。故他以其自身拥有的社会地位,借贬低浙派画名以抬高松江画派的地位,包括吴门画派的一切声名,最终把自己推为继二派之后的画坛领袖。
虽有李开行在《中簏画品》中对浙派绘画表达了赞赏之情,呵护有加,客观地完整地对其加以梳理和评价:但与各种指责浙派的骂声一比,气势明显不够。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各种对浙派绘画艺术的偏见,包括持续到近现代的相关研究内容,不妨说是少之又少。如史论界对浙派绘画的探讨,相对于研究吴门画派或“南北宗论”范围要小得多。再就是一些专业院校在山水画教学内容设置上,学“南宗画法”明显多于“北宗画法”;故使有关戴进、吴伟名字出现的频率远不如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笔者还注意到,在当今个别美术史论专著里,一般不写与浙派绘画研究相关的内容,他们可以谈“逸”,谈“书卷气”,谈文人画艺术领域成就较高并具有影响力相对较远的前前后后不同时期的画家,如王维、董源、苏轼、赵孟頫、倪瓒、沈周、文徵明、八大山人等,但对于戴进、吴伟等浙派画家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够,这种现象极不正常,是否引起大家深思?否则,就难以对整个明代绘画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
(潘丰泉/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