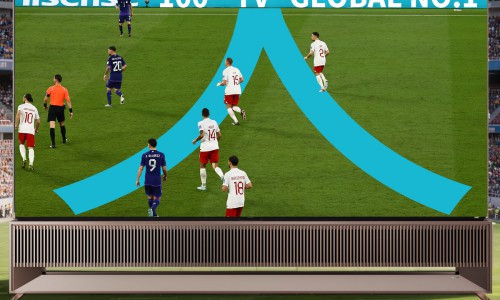王洁
摘 要:陕北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作为当地民俗文化代表之一的老剪纸,它保留了太多古老文化的信息。在民风古朴的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剪纸是陕北人民俗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形式。无论是年节时分,还是嫁娶、生子、丧俗等重要时日场合,剪纸的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它不仅长于烘托气氛,而且能够传达言语不能明示的深刻寓意。
关键词:老剪纸 窗花 喜花 抓髻娃娃 刺绣花样
老剪纸,是相对于现代商业剪纸而言的,一般是指我国早期的民间剪纸,由隐藏在民间的剪纸巧手们剪或刻制而成,包含着古老的寓意,专为当地百姓的民俗生活服务。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广大农村还到处保留着古朴的民俗民风,每逢节日、婚嫁、生死等重要时日,正是各种当地民俗集中演绎的时刻,地处黄土高原黄河西岸的陕北亦不例外。剪纸在陕北的民俗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节日里,它曾将陕北荒瘠的大地装点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按照陕北剪纸在民俗生活中的不同作用,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春节窗花剪纸、人生礼仪剪纸、巫术宗教剪纸和刺绣花样剪纸四大类型。
一、春节窗花剪纸
在陕北人的节日里,除了当地百姓最看重的春节,其它时节很少见到剪纸。
诗人和画家艾青曾写道:“1943年春,我和刘建章、古元同志到三边,沿途看见许多老百姓家的窗户上贴着窗花。”①想必是在春节刚刚过后,艾青和古元一行人到陕北的三边地区采风时看到的景象。
在陕北的广大农村,每逢过年,窑里窑外都要贴上花花绿绿的剪纸,只见那窑洞外的窗户上,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剪纸贴的满满当当,从远处看,大红的剪纸在白色的麻纸和整体土黄色背景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暖和喜庆,走近再看,一幅幅剪纸又如花似蝶,绽放着生命的光彩,把冬日萧条的农家小院装扮的生机盎然,因此,剪纸在陕北被亲切地称为“窗花”。虽然窗花并不限于贴在窗户上,在陕北农家的门楣、墙围、炕头、窑顶、粮仓、米缸、面囤、碗架、柜子、箱子等等,家里每一处能贴的地方都要贴上五颜六色的“窗花”,直到把平日里灰头灰脸的家装扮一新。
春节的窗花内容最为丰富,几乎囊括了陕北剪纸所有的题材内容和花样形式,其中十二生肖动物是陕北大娘最喜爱剪的题材。当地人都习惯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十二种属相进行记年,并根据农历季节安排生产活动,而且由于十二属相中的大多数动物都与农家生活息息相关,受到剪纸大娘们的青睐是很自然的事情。其次,狮、鹿、鸟、鱼这些能辟邪和喻意吉祥的动物也是大娘们的最爱。动物题材的剪纸一般剪成小幅的,正好在每个窗格里贴,有时也与花草组合剪成大幅的团花,在窗户的正中贴上一幅,两边对称再各贴一幅,叫转花。除动物外,花草或单独或与动物、景物等组合成花样,小幅的为窗花,大幅的为窑顶花,生机勃勃,变化万千。戏曲历史或神话传说的题材一般剪成二方连续的形式,以展开情节,当作炕围花,既美化窑洞,又为孩童们的启蒙知识画本。至于粮仓、米缸、面囤处贴些动物和植物组合的图案花,希望来年米满仓面满囤,与此处张贴的对联,如“米面常有”“粮食满仓”等喻意一致。贴在门上的多为狮虎形象,作用等同与关中一带的门神,起辟邪作用。
三边地区的窗花比较特别,包括转花、角花、小窗花等,转花一般剪为四块,贴在窗子中间,四个格子四张,拼贴成圆形或一个完整的动物。转花为中心图案,主要内容有花鸟、麒麟、狮子、老虎。角花为三角形,贴在窗子的四角边上,因花草容易剪成适形图案,内容多石榴、牡丹等。小窗花则自由布满其余窗格,内容以十二生肖为主。
艾青在四十年代到陕北采风时见到“在边区许多老百姓的窗纸上,常常可以看见贴着红红绿绿的剪纸,每张约四五寸见方大小,一张占一格窗格子,剪的是老百姓所熟悉的事物:家畜、家禽、花、鸟、虫、鱼、水果、蔬菜、盆、茶壶、武器、人物以及故事。”②
总之,春节的窗花题材多样,喻意吉祥,花样繁多,是陕北剪纸最为全面的反映。
二、人生礼仪剪纸
婚嫁、生子、丧事都是人生大事,各种礼仪风俗在这些时候表现得最为集中。剪纸在烘托气氛、表达寓意等方面的作用也在这些场合显现出来。
当地人把用于婚嫁时的剪纸都叫“喜花”,内容多与生殖生育有关。把洞房叫“帐房窑”,新媳妇进门先要坐帐,在帐房窑的顶部或炕墙中央要剪一幅整张纸大的转花,叫做“坐帐花”。陕北人结婚,帐房窑内家具可以不放,但坐帐花却不能少。坐帐花由象征生育繁衍的鱼、莲花、牡丹、佛手、南瓜、葫芦、石榴、龙凤及抓髻娃娃等纹样组成,内容都与生殖繁衍有关,表达男女相合,子孙繁衍的象征意义。一般有“娃娃坐莲花(娃娃坐莲花,两口子好缘法)”“坐石榴抱牡丹(石榴抱牡丹,养下一铺滩)”“仙桃莲花(仙桃对莲花,两口子生下个胖娃娃)”“蛇盘兔(蛇盘兔,必定富)” “鹰踏兔” “鱼戏莲”“老鼠吃葡萄(南瓜、西瓜、白菜)”(及“葫芦”“扣碗”等,用充满寓意的艺术形象暗示出生殖繁衍的全部过程,祈盼新人早生子,多生子。
新婚媳妇进入帐房后,新娘新郎背靠背坐在炕上,由一位年长的妇女用木梳将新娘的头发搭在新郎的头上梳理,叫做“上头”。“上头”时还要唱歌谣,而这歌谣正是坐帐花的主题,即祝福新人早生孩子,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帐房内的顶棚花中间为大幅团花,四角为角花,内容多由石榴、佛手、牡丹、等组合。其他还有窗户、炕围及帐房内的家具用具上都贴上大小不等的各式喜花,娘家陪嫁的箱子、柜子、镜子、酒瓶、花馍上也要贴着或盖着“石榴牡丹”、“喜鹊戏牡丹”、“双喜争梅”及对蝶、对鱼、对雀等形象,表达阴阳相合、夫妻成双的民俗观念。
婚嫁中的剪纸与绣品包含着古老且丰富的内容,都围绕着生殖繁衍的主题创作。据老人们讲,过去的人结婚早,不懂事,长辈又不能明讲,“鹰踏兔”、“鱼戏莲”、“扣碗”就是给新婚夫妇以性的启示。结婚用的剪纸多半是请同族中巧手的嫂嫂或是村中的剪花高手来剪。总之,婚嫁剪纸喜花是陕北民间剪纸中除春节窗花外,内容和形式最为丰富多样的剪纸。
孩子诞生多剪各种坐生喜花及“连生贵子”“马上封侯”“麒麟送子”“天鸟送子”等祝福内容,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单一。
在陕北,丧俗剪纸也有很重要。陕北人把儿女结婚和老人过世举办的仪式叫“红白喜事”,“白事”与“红事”一样要过得红火热闹。“白事”中的剪纸及各种纸扎以白色为主,兼有黄、紫、金、银、蓝、绿等各种颜色,唯不能见红色,以素色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以热闹的仪式庆祝生命的轮回,因为当地人认为人死后要投胎转世,还有来生。
陕北有专门制作“白事”用“纸扎”的,当地人称之为“纸活”,儿女们要给去世的老人订做一套“纸活”宅院,有窑洞、炕、磨、碾、牲畜、佣人等等,凡人间有的都有,供老人在冥间享用。装点“纸活”的剪纸,内容多是莲花、石榴、鱼、鹿等象征生命繁衍绵延的纹饰。
三、巫术宗教剪纸
在陕北,春节时每家都在门楣上贴五个手拉手的“瓜籽娃娃”或剪纸“拉手娃娃”,说是能阻止妖魔鬼怪进家们。过年时剪的财神挂帘,以摇钱树、元宝、贯钱、鹿(禄)、莲鱼(连年有鱼)等纹样装饰,有的挂帘剪一个民间传统的大寿字纹,周围用富贵、万字纹和摇钱树相连,有些还用双鱼瓶、双葫芦、蛇盘兔等做装饰;灶君爷挂帘中要剪出灶狗形象,说是小媳妇如在灶君前掼打,灶君将会放出狗咬的。
正月初七是“人日”,陕北人把这天当作扶运气的好日子,剪一只绿色的鹿和一只红色的马,对贴在窑内最显眼的墙上,鹿和马的下方贴上一个用黄表纸做成的三角形香炉。上香的同时,口中还要念叨“马、马你吃草,一年的运气都扶好……”以祈祷事事如意。孩子受到惊吓,母亲剪个“招魂娃娃”,赶到孩子受惊吓的地方,然后一边向回走,一边呼喊“娃儿回来,娃儿回来……”,回到家里之后把剪纸“招魂娃娃”放到娃娃的身上,意味着娃娃的魂就回来了。娃娃生病了,剪个“招魂娃娃”或“送病娃娃”,也要念叨一番“送了头上头上轻,送了脚上脚上轻……”,之后将剪纸焚烧掉。天下连阴雨时剪“扫天媳妇”。
除了阴雨天气剪“扫天媳妇”外,当久旱不下雨时,洛川民间剪一个头朝下的娃娃贴在水缸上,有的地方则剪一串“蛙”沿着水缸口贴上,说是能求得甘露浇灌庄稼,保丰收。
这些应用于各种宗教巫术活动中的民间剪纸,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审美是次要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宗教巫术思想的渗透,作为民俗文化载体的剪纸才能在民间绵延不断,也才有机会创造出美的形象,其丰富且深刻的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涵才得以展示。
由于巫术剪纸的主要目的是治病、镇宅、辟邪,除了用来镇宅辟邪的“狮”“虎”“抓髻娃娃”等要贴在显眼的位置,如门上或墙上,并保留一段时间,而其它的巫术剪纸一般在巫术行为结束之后即刻被焚烧为灰烬,因此,这类剪纸在剪法上古拙简练,只要有个大样,即只注重外轮廓形体的转折、变化、取舍,内部装饰简化甚至完全不要,意到神在,以强调其精神性和威慑力。
四、刺绣花样剪纸
过去的陕北妇女个个都是做针线活的巧手,不仅全家老小的穿戴是一针一线缝制的,还给孩子们绣制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花肚兜、吃饭时用的围嘴等等,把孩子们打扮的古怪精灵,可爱至极。女孩子出嫁时要准备绣花衣、绣花鞋、绣花枕、绣花门帘,纳花鞋垫等等,针针线线都含情,各个花样都寓意深刻。不仅这些,老人去世用的丧衣、丧鞋等等,都要刺绣上各种寓意精美的图案,意味着一个人今生来世都是美好的。于是,剪纸就成了这丰富多样的绣制品的底样,民间称其为刺绣花样,这可是刺绣的第一道工序,没有它,就不可能绣制出各种精美的刺绣图案。
民俗文化的根本在于差异性和独特性,没有了差异也就没有了民俗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民俗文化最终难逃一体化的命运。那些饱含寓意的陕北老剪纸如今几乎绝迹,只因需要它的民俗环境已不复存在,过年的窗花已成为上了年纪的人们儿时的记忆。尽管一些旅游景点还打着民间老剪纸的旗号张贴叫卖,可我们都明白,老剪纸的根是不会在商业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注释:
①②孙新元,尚德周.延安岁月[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4. 引自其中艾青《窗花剪纸》一文(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第518页。
参考文献:
[1]孙新元,尚德周.延安岁月[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2]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3]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